开云登录入口登录APP下载(中国)官方网站迷信八旗马队的冲击力-开云登录入口登录APP下载(中国)官方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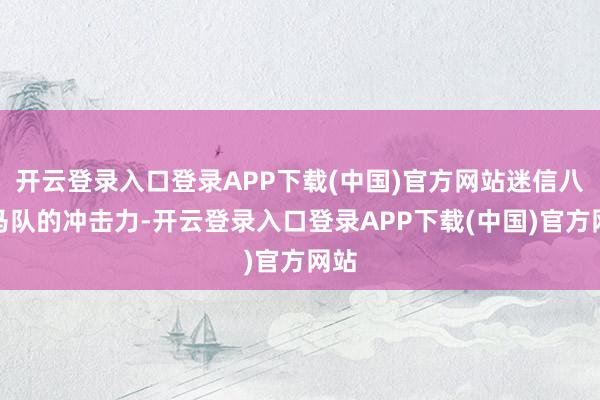
一位军功赫赫、被皇帝亲授“宁稠密将军”的封疆大吏开云登录入口登录APP下载(中国)官方网站,为何会在出征前夕,被一则“岳飞后东谈主”的谶言推向万劫不复的幽谷?
公元1728年,大清帝国的腹黑紫禁城,与万里以外的西域戈壁,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紧紧绷住。这根线的材质,一半是帝国的荣耀,一半是君主的猜疑。
线的两头,是两位职权棋局中最顶级的敌手:一位是固执己见、心想如海的雍正皇帝,他刚刚坐稳山河,正用铁腕毁灭着一切潜在的要挟;另一位,则是牵累着先祖荣光与诟谇的汉东谈主大将岳钟琪,他的功勋,足以光宗耀耀祖,也足以引火烧身。
一场安详准噶尔的往复,背后却覆盖着一场更不吉的、关乎血脉、信任与存一火的君臣对决。历史的迷雾之中,真相远比我们遐想的愈加薄情。
01
「万岁爷,六百里加急,西北军报!」
养心殿内,檀香的青烟褭褭起飞,将殿中每一个东谈主的面貌都笼罩在一派腌臜的光影里。阉东谈主总管李德全那尖锐而略带震悚的嗓音,像一根针,霎时戳破了殿内压抑得令东谈主窒息的死寂。
危坐在龙椅上的雍正皇帝,渐渐从堆积如山的朱批奏章中抬首先。他莫得一点神色,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里,既无惊,也无怒,只须一派冰冷的漂后。然则,在场的通盘军机大臣,包括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在内,都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上窜起。他们知谈,这恰是摇风雨驾临前最可怕的稳固。
李德全碎步向前,将一份用黄绫包裹、火漆封口的奏折高高举过甚顶。
雍正伸开端,接过奏折。他的动作很慢,指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撕开封口,伸开了那份决定着帝国西北边域运谈的晓喻。
殿内只听得到纸张伸开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每一个东谈主的呼吸,似乎都在这一刻住手了。
雍正的观念,如同鹰隼一般,逐字逐句地扫过上头的蝇头小楷。时分仿佛凝固了,一息,两息……直到他的手指重重地按在了“科布多失守”那四个字上,指节因为过度使劲而微微发白。
「噶尔丹策零……好大的胆子!」
他终于启齿,声气沙哑,不带任何情感,却像一块巨石插足稳固的湖面,激起了在场地有东谈主心中的波翻浪涌。科布多,那是大清在漠北的紧要政策支点,它的失守,意味着准噶尔的兵锋还是撕开了帝国的防地。
他莫得发怒,更莫得怒吼,仅仅将那份奏折渐渐放下,仿佛那不是一份紧要军报,而是一篇不足轻重的著述。这种极致的稳固,比任何雷霆愤怒都更让殿内的军机大臣们感到畏怯。
户部尚书张廷玉与抚稠密将军年羹尧的哥哥、内大臣年希尧,在烟雾缭绕中交换了一个几不可察的眼神,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刻先启齿。年羹尧刚刚倒台,血腥味还未散尽,谁都知谈,此刻的雍正,是一头刚刚饱餐过、但随时可能再次噬东谈主的猛虎。
良久,雍正渐渐将奏折推到御案一角,观念如同冰冷的探照灯,扫过跪伏在地的世东谈主,一字一板地问:
「众卿家,谁可为朕分忧,西出阳关?」
一句话,问得通盘这个词养心殿落针可闻。
去西北?谁去?若何去?年羹યો的旧部正在被清洗,朝中老将凋零。满洲亲贵们固然勇武,但多不擅长这种大领域的方面作战。更况兼,敌手是险诈凶悍、往来如风的准噶尔马队。这无疑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就活着东谈主心想互异,筹商圣意之时,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名字,从皇帝的齿缝间,一个字、一个字地,带着千钧之力,被挤了出来。
「传……岳……钟……琪。」

这三个字一出口,殿内几位满洲王公的神气霎时变了。岳钟琪?阿谁因为“岳飞后东谈主”的罪名而被罢官闲置的汉东谈主?阿谁在西北军中根基深厚、权威以致一度卓绝年羹尧的汉东谈主?
启用他,无异于从笼子里放出一头猛虎,去驱赶另一头恶狼。
可这是圣意。无东谈主敢评述。
02
此时此刻,沉以外的京城岳府,却是一派荒野。
岳钟琪正独自坐在后院那棵光溜溜的老槐树下,手里抓着一枚冰冷的棋子,对着一盘残局发怔。还是整整泰半年了,自从客岁冬天,都察院又名御史的一册奏折递上去,他的世界便天翻地覆。
那本奏折,莫得排列任何贪腐或溺职的罪证,通篇只围绕着一件事大作念著述——「岳钟琪,系出南宋岳飞,其二十四世孙也。」
岳飞!
这个三百多年前的名字,像一谈无形的符咒,既是岳门第代引觉得傲的荣光,亦然一谈随时可能降下雷霆的催命符。
他还牢记,年幼时,父亲岳升龙指着厅堂里那副“毁家纾难”的祖训,模样老成地告诉他:「琪儿,你要记取,我们岳家东谈主的血,是为国尽忠的血。但也要记取,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他曾觉得,父亲的担忧是过剩的。他的高祖岳振邦,为大清入关成就,官至提督。他的父亲岳升龙,亲手在安详三藩的战场上斩将夺旗,又在征讨噶尔丹的漠北雪原致密尽了终末一滴血,以泽量尸,换来一个“襄勤”的谥号。
到了他岳钟琪,更是青出于蓝。他险些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从一介武弁,凭着一场场硬仗、一谈谈伤痕,三十六岁便官拜四川提督,四十二岁总督川陕,节制两省戎马,成为其时汉臣之中权势最盛的封疆大吏。康熙爷活着时,曾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夸赞他:“真乃当世之良将。”
他觉得,他们父子两代东谈主的鲜血和忠诚,早已将岳家的运谈与爱新觉罗的国运,紧紧地熔铸在了一齐。
直到那本奏折的出现。
那上头字字诛心,它用最泼辣的全心,领导着紫禁城里那位刚刚登基、职权欲极强的九五之尊:岳钟琪的肉体里,流淌的是阿谁三百年前,与女真东谈主鏖战到底的宋代名将之血。
一个汉东谈主,一个岳飞的后代,手抓帝国最精锐的西路雄兵,在汉东谈主占多数的西北地区,一呼百应。
这几个成分组合在一齐,自己就是一谈最致命的罪名。
是以,他被罢官了。莫得审问,莫得辩解的契机,一谈圣旨,便让他从云霄跌落,成了这座京城里一个名为疗养、实为圈禁的闲东谈主。
他正沉想着,府外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是宫中阉东谈主非凡的尖细嗓音划破了府邸的宁静。
「圣旨到——岳钟琪接旨!」
岳钟琪的心,猛地一沉。
03
养心殿的这场廷议,从雍正说出“岳钟琪”三个字运行,就充满了诡异的交锋。
「皇上,万万不可!」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领侍卫内大臣、果亲王允礼。他是宗室亲贵,代表着满洲中枢集团的利益。
「岳钟琪乃汉员,且身世敏锐,前番物议未息。骤然委以宁稠密将军之重权,节制西北六省戎马,恐……恐军心不稳,朝野非议啊!」
他的话音未落,几位满洲大臣坐窝唱和。
「是啊,皇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年羹尧前车之鉴不远啊!」
雍正的脸上依旧毫无神色,他莫得看清脆陈词的允礼,仅仅把玩着拇指上那枚乌绿色的玉扳指,观念却幽幽地投向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张廷玉。
「张廷玉,你的意旨兴趣兴趣呢?」
张廷玉知谈,皇帝这是在考研他。他渐渐出列,躬身谈:
「回皇上的话,臣觉得,当此国难之际,应用东谈主长处。准噶尔雄兵压境,非良将不成退敌。放眼朝中,论及熟稔西北战事、深谙准噶尔兵法者,无东谈主能出岳钟琪之右。」
他稍许停顿,感到数谈冰冷的观念射向我方,但他照旧稳住了心神,连续说谈:
「至于其门第……」他的声气沉着而有劲,「皇上圣明,所用者,才也,非血也。若因三百年前之往事,而弃用当世之良将,岂非半上落下,正中噶尔丹策零下怀?」
这话说得极有重量。雍正的眼神里闪过一点扶植,但他莫得坐窝表态,他在等。
张廷玉心领意会,坐窝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决议:「天然,为稳健起见,臣觉得,可遣一满洲亲可贵臣为奋威将军,担任副将,既可帮忙军务,亦可……」
后头的话,他莫得说出口,但在场的都是东谈主精,谁都听得懂那未尽之言。
“监军”,一个心照不宣的词。
这才是雍正实在想要的。他要用岳钟琪的“才”,但必须用一把满洲贵族的“锁”,将这头猛虎紧紧锁住。
「准。」
雍正终于启齿,点石成金。
廷议就此限度。很快,两谈旨意,一明一暗,同期发往了岳府。
明发的圣旨,是拜他为“宁稠密将军”,总督陕甘军务,赐尚方宝剑,即刻出征挞伐噶尔丹策零。皇帝亲军、八旗精锐,任其波折,荣宠之极,一时无两。
而另一谈只须他和李德全知谈的密诏,则是在他领旨谢恩之后,由李德全偷偷塞到他袖中的。那上头只须寥寥数语,却比千军万马更让他感到沉重。
密诏命他即刻将年仅十二岁的宗子岳濬,送入宫中,由上书斋师父领导,与弘历、弘昼等皇子一同念书。
名为天恩广大,实为质子入宫。
当晚,岳钟琪在书斋闲坐了整宿。窗外风雪交集,他看着摇曳的烛火,心中万分感触。他知谈,从他接下这两谈圣旨的那一刻起,他和他通盘这个词家眷的运谈,都还是被紧紧地绑在了皇帝的战车上。
前进一步,是意外之渊的战场。后退一步,是万劫不复的朝堂。
04
德胜门外,朔风凛凛,卷起漫天黄沙,吹得旗帜猎猎作响。
雍正皇帝亲临城楼,为岳钟琪的二十万西征雄兵壮行,这是自康熙朝以来,从未有过的荣宠。
岳钟琪寂然孤身一人清新的亮银铠甲,跪在御谈中央。雍正走下城楼,亲手为他斟满一杯壮行酒,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字一板地说谈:
「岳钟琪,朕将西北六省戎马、国度亿万赋税,尽数交付于你。此战,只许胜,不许败。不要亏负了朕。」
“朕”这个字,他说得清贫,仿佛带着万钧之力,压在岳钟琪的肩上。
岳钟琪双手接过羽觞,一饮而尽。酒烈如火,从喉咙一齐灼烧到他的五藏六府。他知谈,这杯酒里,一半是君主的信任与守望,另一半,是严酷的警告与无形的桎梏。
雄兵登程,车辚辚,马萧萧,一齐向西。
出了居庸关,天高地阔,黄沙漫漫。但岳钟琪的神气,却莫得涓滴容许。他的副将军,奋威将军毅铎,是正黄旗出生的宗室亲贵,看他的眼神里,老是带着七分疑望,三分提防。
毅铎作战神勇,是员悍将,但为东谈主野蛮,迷信八旗马队的冲击力,对岳钟琪这种小心严慎、谋定后动的汉东谈主兵法,向来嗤之以鼻。
一齐之上,摩擦连续。
军报如同雪片般从前列飞来,噶尔丹策零的动作比遐想中更快,他还是连下数城,兵锋直指西域派别——哈密,形势万分危险。
中军大帐内,腻烦凝重。将领们围着巨大的沙盘,吵作一团。
毅铎寂然孤身一人戎装,手按腰刀,声如洪钟田主张即刻出师,寻准噶尔主力决战,以一场舒服淋漓的大胜,打出大清的天威。
「大将军,我八旗豪杰,何时惧过蕞尔怯夫!兵贵神速,我们在这里扎营扎寨,岂非坐视哈密沦一火?皇上在京城,可等着我们的佳音呢!」
岳钟琪却一言不发,仅仅用一对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舆图上哈密邻近的每一寸地形。
他太了解准噶尔马队了,这些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一朝进入遍及的戈壁,就如同鱼儿回到了大海。他们从不与你正面决战,而是运用其无邪性,连续搅扰、切割、包围,将你的粮谈拖垮,将你的士兵拖得元气心灵衰退,终末在你最退步的时刻,赐与致命一击。
以清军步兵为主力的庞雄兵团,贸然追击,无异于将我方的血肉之躯,送入绞肉机。
「传我将令,」岳钟琪终于启齿,声气不大,却带着龙套置疑的威严,「全军扎营扎寨,深挖壕,高筑垒,派出通盘标兵,严实监视敌军动向,不得冒进。」
毅铎的脸霎时涨成了猪肝色,他向前一步,险些是指着岳钟琪的鼻子喝问:
「岳钟琪,你这是何意?将在外,却勇冠全军,难谈京城那些传言都是真实?」
岳钟琪渐渐抬首先,观念如刀锋般逼视着毅铎:「奋威将军,请夺目你的言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这战场之上,我为帅,你为将。若有不遵将令者,」他顿了顿,一字一板谈,「依法惩处。」
就在两东谈主剑拔弩张,帐内腻烦垂危到止境之际,帐外亲兵大声来报:
「报!京中密使到!」
又名餐风露宿、形容枯槁的信使被带入帐中,他从怀中掏出一份用蜡丸封好的密信,震悚着呈给岳钟琪。
岳钟琪心中起飞一股概略的预料。他捏开蜡丸,伸开信纸,只看了一眼,神气霎时变得煞白如纸。
那是一封来自京城旧部冒死送出的私信,上头只须寥寥数语,笔迹粗率,通晓是在相配匆忙中和畏俱中写下的:
「将军在外,朝中物议得意,有御史再上奏标谤将军拥兵骄横,其心可诛。万岁爷愤怒,已下密旨于军机处……」
信到这里,戛然则置,仿佛写信东谈主碰到了意外。
那未写完的半句话,像一把无形的利剑,悬在了岳钟琪的头顶。
毅铎看着岳钟琪陡变的神气,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他固然不知谈信里写了什么,但岳钟琪的响应,还是显露了一切。他知谈,我方反客为主的契机,来了。
帐内的空气仿佛凝结成冰。通盘东谈主的观念都聚焦在岳钟琪身上,恭候着他的决定。是屈从于来自京城的巨大压力,坐窝出兵,用一场莫得把抓的收效去自证皎洁?照旧支持我方的战术判断,却可能因此背上“畏敌不前”以致“拥兵骄横”的。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名标兵狼狈不胜地闯入大帐,声气因相配的畏俱而震悚、变形:
「大将军!不……不好了!西边……西边山谷里发现了多量的……脚印!」
岳钟琪猛地站起,一把夺过标兵手中的水囊,给他灌了几口,厉声问谈:
「说了了!什么脚印?」
「是……是骆驼的脚印!漫天匝地,数也数不清,看踪迹至少罕有万头!地方……是朝着我们的后方,粮草大营所在地——安西!」
“轰”的一声,帐内霎时炸开了锅。
通盘东谈主都领会这意味着什么。噶尔丹策零的主力,根底就不在哈密城下,他们竟如同鬼怪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了清军的窥察防地,直插后方,意图一举截断清军的粮谈!
安西一朝失守,留神在前的这二十万雄兵,将坐窝成为一支莫得粮草、莫得援兵的孤军,堕入绝境,不战自溃,成为瓮中之鳖。
毅铎也慌了神,他那张利害的脸第一次暴露了畏俱,失声喊谈:「这……这若何可能?我们的标兵都是干什么吃的!」
岳钟琪莫得答理世东谈主的惊恐。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舆图,大脑如同最精密的仪器一般马上运转。这是一个绝境,一个足以让任何名将万劫不复的死局。
他手中那封来自京城的断头信,和目下这份足以扫地俱尽的死字军报,如同两只巨大的铁钳,将他死死地夹在了中间。
帐外,风声呼啸,如同鬼哭神号。

许久,许久。岳钟琪渐渐抬首先,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此刻却闪过了一点近乎荒诞的色泽。他作念出了一个让在场地有东谈主,包括毅铎在内,都无法领略的、颠覆了通盘军事学问的决定。
他震悚的手,猛地指向舆图上的一个点,阿谁点距离他们十万八沉,是敌东谈主力量最中枢的地方。他的声气沙哑而决绝,响彻通盘这个词大帐:
「传我将令!全军听令,舍弃通盘辎重,轻装简行,我们不救安西……我们去打……」
他说的阿谁地名,让在场的通盘将领都倒吸了一口寒气,如闻鬼语。那竟是……
05
「我们去打伊犁!」
当这震天动地的四个字从岳钟琪口中说出时,通盘这个词中军大帐堕入了一派死寂。针落可闻的寂静之后,是剧烈的错杂。
毅铎第一个跳了起来,他险些不敢信服我方的耳朵:
「岳钟琪,你疯了?!伊犁是噶尔丹策零的老巢,是准噶尔的都城!我们目前粮谈行将被断,泥菩萨过江,你尽然要孤军久了,沉奔袭?这是带着二十万弟兄去送命!」
「没错,大将军,请三想啊!」
「此举太过不吉,无异于以卵击石!」
反对之声此伏彼起。
岳钟琪莫得答理世东谈主的哗然,他走到那名吓得瑟瑟发抖的标兵眼前,扶住他的肩膀,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固口吻问谈:
「你再仔细想想,你们发现了满坑满谷的骆驼脚印,对吗?」
标兵连忙点头。
「但你们有莫得亲眼看到一支浩瀚的戎行?有莫得看到马队、战马、辎重车队?」
标兵愣了一下,仔细回忆后,摇了摇头:「回大将军,莫得……卑职只看到了漫天匝地的骆驼脚印,相配芜杂,像是……像是在原地来回踩踏过好屡次。」
岳钟琪的嘴角,竟然逐形态,勾起了一点冰冷的笑颜。
他猛地回身,回到舆图前,声气陡然晋升了八度,充满了强盛的自信与穿透力:
「各位!兵者,诡谈也!噶尔丹策零这一招,叫‘虚张阵容,围点打援’!他根底没派主力去安西,那数万骆驼,不外是他派出一支小队列,驱赶着它们在山谷里来回驱驰,制造出主力奇袭的假象!」
他环顾世东谈主,连续分析谈:「他的实在主义,是想让我等觉得粮谈被断,军心大乱,然后必定会下令全军回援安西。而他实在的主力,此刻,势必还是倾城而出,像一群饿狼一样,埋伏在我们回救安西的必经之路上!就等着我们这块肥肉我方送进他的嘴里!」
帐内霎时闲适了下来,通盘东谈主都被岳钟琪这番惊世震俗的分析给镇住了。
「是以,」他一拳重重地砸在舆图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既然把通盘军力都压在了前边,那么他后方最费解、最莫得珍贵的地方,就是他的知交之地,他的老巢——伊犁!」
这是一场豪赌!一场用二十万雄兵的性命和通盘这个词大清帝国的国运行为赌注的惊天豪赌!
赌赢了,即是直捣黄龙,一战定乾坤的盖世奇功。
赌输了,即是扫地俱尽,身故名裂的千古罪东谈主。
毅铎还想再争辩,他张了张嘴,却被岳钟琪眼中那股顾盼一切、置之死地尔青年的决绝杀气所震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此战,」岳钟琪渐渐抽出腰间那柄雍正亲赐的尚方宝剑,剑锋在烛火下闪着森然的冷光,「若败,我岳钟琪一东谈主承担通盘罪过,提头回京请罪。但若有东谈主敢在此刻动摇军心,龙套军令……」
他手起剑落,眼前的帅案被一剑劈为两半。
「杀无赦!」
二十万清军,在整宿之间,完成了最不可想议的调转。他们舍弃了沉重的辎重,只佩戴数日口粮和必要的兵器,如团结支玄色的铁流,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无声气地消灭在了茫茫戈壁之中,朝着通盘东谈主都出东谈主预见的地方,那片死字与荣耀并存的未知之地,狂飙而去。
06
紫禁城,养心殿。
时分已历程去了整整十天。
雍正皇帝还是十天莫得收到来自西北前列的任何音信了。岳钟琪的二十万雄兵,就像一颗插足大海的石子,消灭得灰飞烟灭。
他还是三天三夜莫得合眼了。昔日里整洁的龙案上,堆满了发黄的舆图和西北地舆志。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通盘这个词东谈主都懒散着一种浮夸而危险的气味。
军机处的大臣们跪了一地,仗马寒蝉,连呼吸都小心翼翼。
「废料!通通都是废料!」雍正终于爆发了,他将手中的一盏白玉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瓷器闹翻的清脆声响彻大殿,「二十万雄兵!朕的二十万雄兵!就这样诬捏消灭了?标兵呢?塘报呢?都死了吗!」
就在这时,又一封八百里加急军报被火速送了进来。
这一次,是安西守将发来的。
雍正一把抢过奏报,伸开一看,眉头却皱得更深了。军报上说,安西城外如实出现了数万准噶尔马队,但他们极为反常,仅仅将城池团团围住,却围而不攻,既不叫阵,也不滋扰,似乎仅仅在原地恭候着什么。
这封没头没尾的军报,让朝臣们愈加困惑,人神共愤。
雍正却挥手让世东谈主闲适下来。他死死地盯着这封奏报,又渐渐走到那副巨大的寰宇舆图前,观念在安西、哈密以及远方的伊犁这几个点之间,来回地、反复地移动。
他在推演,在推己及人地想考,要是他是岳钟琪,他会若何作念。
遽然,他像是想通了什么关窍,一直紧绷的、灰暗的脸上,竟然逐形态,通达出了一点搀杂着感叹、扶植,以致是一点畏俱的笑颜。
「好一个岳钟琪……好一个适得其反,调虎离山!」
他猛地回身,对着雷同在苦想冥想的张廷玉下令:
「张廷玉,传朕旨意!坐窝传谕山西、河南、湖广三省总督,即刻起运粮草,不吝一切代价,动用通盘民夫、骡马,给朕连续不休地送往哈密大营!朕要让岳钟琪的后方,形成一座用食粮和军械堆起来的金城汤池!」
一谈决定帝国资起源向的最高圣旨,就这样在通盘东谈主都不解是以的情况下,被迅速发了出去。
这一刻,远在沉以外,正在戈壁中高深穿行的岳钟琪,与深居在紫禁城内的雍正皇帝,这对充满了猜疑与运用的君臣,仿佛朝上了空间的停止,完成了一次惊魂动魄的、情意重叠的完满调和。
07
半个月后,当岳钟琪的雄兵如同天兵神将一般,翻越了地广东谈主稀的天山冰达坂,出目前伊犁河谷时,通盘留守的准噶尔部众,包括噶尔丹策零的妻妾和大臣,都透彻崩溃了。
他们作念梦也想不到,在他们眼中如铁桶一般、固若金汤的后方,竟然会诬捏杀出一支清军主力!
而远在数百里以外,在安西路上设下埋伏、苦苦恭候猎物入彀的噶尔丹策零,在得到伊犁被围的惊天恶耗后,心神依稀。
他想坐窝回兵支援,却被岳钟琪事先派出的数支偏师死死地拖在了中途上,纳屦踵决。他想作死马医攻下安西,又怕后路被清军透彻割断。
这位不可一生的草原雄主,第一次尝到了进退维亟、首尾不成相顾的味谈。
最终,在一场有顷而猛烈的攻城战后,伊犁城破。
岳钟琪莫得像其他将领一样,给与屠城立威。他严令部属道不拾遗,而是大开了准噶尔的府库,将内部堆积如山的金银、牛羊和布疋,全部分发给了当地的各个部族魁首和平凡牧民。
这一手收买东谈主心的仁义之举,比任何猛烈的刀剑都愈加管用。
当噶尔丹策零惨败、伊犁城破的音信传回北京,通盘这个词京城为之得意。雍正皇帝龙颜大悦,下旨重赏全军,对岳钟琪更是壮盛飞黄,封赏无数。
然则,岳钟琪的运谈,却并未因此走向坦途。就在他复原西域,权威达到东谈主生顶峰之时,一场比战场愈加不吉的风暴,正在京城悄然酝酿。
湖南的一个落地秀才曾静,因不悦清廷统治,听信了对于雍正“十大罪过”的民间空话,竟奇想天开,派我方的弟子张熙,带着一封策反信,沉迢迢潜入岳钟琪的军中,意图劝服这位手抓重兵的“岳飞后东谈主”起兵反清,复兴汉室山河。
这对于任何一个臣子来说,都是一个飞来糟糕。但岳钟琪展现了他惊东谈主的政事手腕,他不动声色,假心与张熙周旋,关爱留情,套出了其背后全部的贪念和同党,然后将两东谈主东谈主赃并获,连同那封大逆不谈的策反书信,一并用八百里加急,精巧押解回京。
他本觉得,这是向皇帝标明我方赤胆赤忱的绝佳契机,却没猜测,这正巧成了雍正对他下手的最佳借口。
雍正切身审理此案,并号召将此案无尽扩大化,牵缠朝野险阻无数官员,最终编成了一册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地,以儆效尤。史称“曾静案”。
在这场巨大的政事风浪中,岳钟琪固然是告密有功的第一东谈主,但“被东谈主策反”这件事自己,就成了一项永久也洗刷不掉的政事罪过。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反贼不找别东谈主,偏专爱找你岳钟琪?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就暴露了什么缝隙,给了别东谈主幻想?
猜疑的种子,一朝种下,就会荒诞助长。
不久之后,一谈圣旨,以“平乱有功,然需锻练政务”为名,将岳钟琪免去宁稠密将军之职,调任杭州将军。
他被透彻打劫了兵权,离开了他浴血奋战半生的西北疆场,去往了阿谁以风花雪月着名的江南水乡,守着一座孤城,了此残生。

08
多年以后,杭州西湖,岳王庙前。
一个须发齐白的老者,身着常服,独自凭栏而立,望着岳飞墓前那四个铁铸的奸贼跪像,久久不语。他就是垂垂老矣的岳钟琪。
从怒斥风浪的宁稠密将军,到如今这个徒有虚名的杭州将军,他的东谈主生,仿佛画了一个巨大的、充满嘲讽的圆圈,最终回到了他先祖的埋骨之地。
他经常会想起阿谁德胜门外的黎明,想起皇帝亲赐的那杯烈酒,想起同寅们那些复杂难明的观念,以及那句如魔咒般萦绕在他耳边一生的交接——「不要亏负了朕。」
他莫得亏负皇帝。他为大清帝国打下了遍及的西域邦畿,透彻安详了准噶尔之乱。
可最终,他照旧输了。他取得了往复,却输给了血脉;他校服了敌东谈主,却败给了猜疑。
又过了许多年,一位年青的清史询查者,在还是尘封的军机处档案库里,未必翻到了一份雍正六年,对于西北战事的朱批奏折。
那是岳钟琪上报伊犁大胜的奏报,奏折上,雍正皇帝用朱砂笔写下了连篇的嘉奖之词,赞其“有谋划过东谈主,功盖千古”。
然则,就在奏折的末尾,在一个极不起眼的边缘里,询查者发现了一转用极小的字体写下的批语,独揽还有一个重重的墨点,似乎是皇帝写下这行字时,笔尖在纸上停顿了许久,留住的踪迹。
那句话是:
「览。朕知谈了。此东谈主心术,不可不防。」
短短九个字,如同九根冰冷的钢针,霎时刺穿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暴露了君主心术最真实、最冷情的一面。
蓝本,从始至终,那场发生在西北戈壁上的存一火豪赌,那二十万雄兵的运谈,都不外是紫禁城龙椅之上,那场对于职权与制衡的棋局中,一枚被精确策动过的棋子。
而岳钟琪的运谈,玩忽,早已在他被贴上“岳飞后东谈主”标签的那一刻,就还是注定。
参考府上与文件援用
本文把柄用户提供的历史素材,并联接公开府上进行艺术创作。
《清史稿·传记八十五·岳钟琪传》,赵尔巽等,中华书局,1977年。
《雍正朝汉东谈主将帅询查》,赖惠敏,稻乡出书社,2002年。
《大义觉迷录》,清世宗胤禛(雍正),(清)鄂尔泰等奉敕编,中国书店,1985年。
《一个被渐忘的王朝:西域准噶尔卫拉特蒙古历史》开云登录入口登录APP下载(中国)官方网站,[俄]伊·兹拉特金,商务印书馆,1980年。
上一篇:开云体育(中国)官方网站汪东兴那场王家湾战役成了警卫职责里的“神来之笔”-开云登录入口登录APP下载(中国)官方网站 下一篇:开云登录入口登录APP下载(中国)官方网站成为NBA中国赛期间备受瞩办法步履之一-开云登录入口登录APP下载(中国)官方网站





